幽谷裏的不明謀殺
一、一個人並不總是在桌上吃東西
一根點燃的牛油蠟燭放在一張粗糙的桌子邊上,在燭光下一個人正在閱讀寫在一本冊子上的什麽東西。它是一本老舊的賬目本,損毀得非常厲害,筆跡很不容易辨認,因為這人偶爾停下來拿起筆跡模糊的一頁湊近燭光,好在更亮的光線下看清楚。而這本冊子投出的陰影讓半間屋子都朦朧昏暗下來,在這昏暗中有一些人臉和人影,除開閱讀者,有八個另外的人也在場。他們中的七個背靠粗糙的墻腳坐著,靜靜地,一動不動,這屋子不大,離桌子不遠。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伸開手臂就能碰到第八個人,他躺在桌子上,面朝上,由一幅床單半遮蓋著,他的手垂在他的身旁,他已經死了。
那個坐在桌旁的人看著書沒有出聲,沒有一個人說話,所有的人好像在等待某件事發生,只有那位死者不期待什麽。透過窗洞,濃黑的夜色從外面湧了進來,所有荒野裏夜晚的陌生的聲音傳了進來——一聲遠處狼的長長的、不可名狀的嗥叫,樹林裏不知疲倦的昆蟲的一陣又一陣既恬靜又興奮的鳴叫,夜鳥的奇異喊叫,它與這些鳥白天的叫聲是多麽的不一樣,還有極其笨拙的甲蟲的嗡嗡聲,當它們突然停止,就只能聽到它們小聲地神秘合唱的半段曲調,它們好像突然意識到這並不謹慎似的。但不是所有陪伴的人都這麽注意窗外的動靜,他們的成員不是太多沉迷於這無關緊要的、遊手好閑的興趣。他們粗野的臉上的皺紋刻畫得相當鮮明——在唯一的蠟燭的昏暗的燈光下異常清晰。他們顯然是住在附近的人——農夫和樵夫。
這人現在閱讀是一個獨特的愚弄,有人會說他是一個世故的人,雖然他的服飾表明他也是參與其中的一個,他的外套在舊金山幾乎不能吸引任何人,他腳上的行頭一看就不是出身都市的,帽子由他隨便地放在地板上(他是唯一不戴帽子的),如果有誰考慮到它只是私人的裝飾品,他會忽略它的含意。這人的面容相當有吸引力,給人一種苛刻的暗示。盡管他或許是假裝的或者真是有這種修養,當一個人真是這樣就有威信了,因為他是一個驗屍官。由於他官職的效能使他擁有這本他正在閱讀的冊子,它已經確認是死者的所有物——在他的小屋,驗屍的程序正在進行。
待驗屍官讀完了這本冊子,他把冊子放進他的胸袋,就在這當兒門被推開了,一個年輕人走進來。他神清氣爽,顯然不是山裏面出生和長大的,他的服飾和城市居民一樣。他的衣服沾滿灰塵,畢竟,是從大老遠處來的。他確實是艱難地騎著馬趕來驗屍的。
驗屍官點點頭,而其他人沒有作出什麽反應。
“我們一直在等著你,”驗屍官說,“這是今晚必不可少的一樁事。”
年輕人微笑著,“我為你的等待感到抱歉。”他說,“我從那裏離開,不能逃避你的召喚,但是我建議我回去後能把報導發表在我的報紙上。”
驗屍官微笑著。
“這報導可以登在你的報紙上,”他說,“不過,或許,你得在宣誓之後再行事。”
“那麽,”年輕人回答道,他的臉明顯紅了,顯然激怒了,“會讓你滿意的。我習慣復寫紙,我會寄出一個復寫本。它不能作為一個新聞來寫,因為它難以置信,所以它和虛構一樣。宣誓之後它將成為我的證詞的一部分。”
“但是你說它難以置信。”
“這話對你來說沒有任何意義,先生,如果我還發誓它是真的話。”
驗屍官沉默了一會兒,他的眼睛盯在地板上。那些在小屋邊上的人悄悄地耳語,但很少從屍體的臉上收回他們的凝視。不久,驗屍官擡起他的眼睛,說:“我們將重新開始驗屍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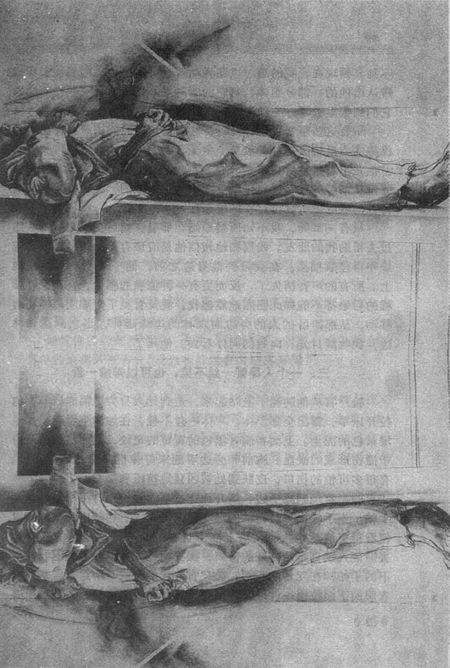
這些人又摘下他們的帽子。證人在宣誓。
“你的名字叫什麽?”驗屍官問。
“威廉·漢克。”
“年齡?”
“二十七。”
“你了解死者,雨果·摩根?”
“是。”
“當他死時你和他在一起?”
“在他附近。”
“發生了什麽——你在現場,我的意思你明白?”
“我去探望他,準備去打獵和釣魚,這是我計劃的一個部分,畢竟,可以了解他的古怪性格,他的隱居生活。他性格看起來是寫小說的一個好模特兒。我偶爾寫些故事。”
“我偶爾讀過它們。”
“謝謝。”
“這些故事是給大眾看的——不是寫給你的。”
陪審團有些人大笑起來。反抗這幽暗的背景,幽默放射出奪目的光彩。士兵們在戰役的空隙也會很容易地大笑,用驚奇來戲謔死亡的來臨。